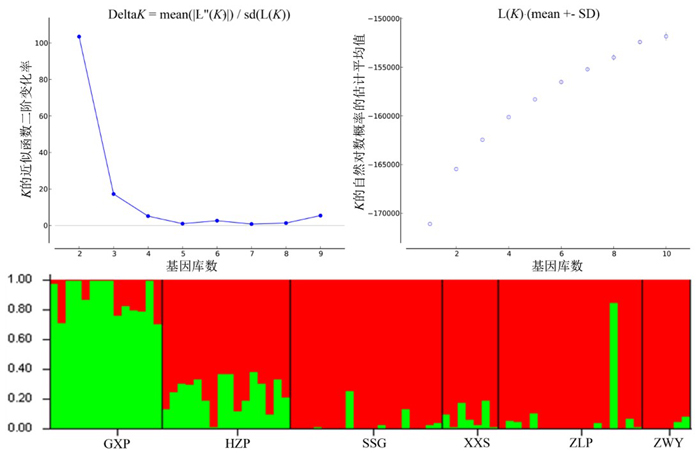火杜鹃
窗外阳台上的一盆杜鹃花, 开得象一蓬火, 它燃烧着, 在我心里。这盆杜鹃花来自山野, 带着泥香和山歌的音韵。这是五岭山区的杜鹃花。只有五岭山区的杜鹃花, 才会这样红艳, 这样热烈, 这样撩人乡思呵!我的故乡不在五岭山区, 但我年轻时曾在五岭山区当过土改工作队长。那时我第一次看到了杜鹃花。从此, 杜鹃花就和着山里人淳朴的笑脸与亲切的乡音, 印在我的脑际。三十几年来, 每当看到杜鹃花, 我就禁不住想起那几个散布在高山大峒中的小村落。我常常想起我的土改“根子”钟树有, 想起山民们选出的第一任乡长刘志顺, 想起树有的邻居、那个会编竹器的、后来当了民兵队长的青年钟长兴; 想起许许多多在我们“翻身分田地, 当家做主人”的鼓动下, 由犹豫、兴奋, 进而抱着无尽的希望走向新生活的山民们。钟树有年近五十, 是个乐天派, 同谁都开玩笑, 全村无论大人小孩, 辈分高低, 都戏称他“老有”, 其实他什么也没有, 是个连老婆都没有的老光身汉。家徒四壁, 只有一条猪, 一只破锅和一张破网一样的褐色棉套子。他满脸皱纹, 样子很衰老, 但生性快活, 很喜欢唱山歌。冬夜, 我俩常被一阵阵寒气推醒, 从那张破网般的棉套子里钻出来, 坐在灶头, 拢一把火, 把陶罐放在火堆上, 煮一罐粗茶, 一面聊天, 一面啜饮苦涩的浓茶取暖。我问起他的过去, 问起他那很久很久以前曾经在他的生活中闪过一点亮光的相好。他有时用话来回答, 有时就轻轻地唱起山歌。他这个人有点怪, 谈再悲惨的事, 脸上总挂着木然的笑; 一唱山歌, 两眼就涌满泪水。我问他为什么唱得这般苦, 他说因为山歌是从心里流出来的……春天来了, 土改进入分配阶段, 山民们的情绪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钟树有甩掉拿了一冬的破手笼, 脱掉穿了一冬的破长袍, 象山上的野草, 活力在身上暗暗恢复过来, 样子显得年青了。一天我同他上山砍竹, 看到山道旁有许多红色的花, 再向远望, 层层叠叠的山峦都披上了红彩; 只几天工夫, 大地就变了样, 变得如此壮丽!我惊讶了, 顺手采了一枝花问: “老有, 这是什么花?”“杜鹃花, 又叫映山红。”“呵, 这真是杜鹃花吗?”我望着山火一样燃烧的花丛。“是杜鹃花。”他说。接着, 他放开嗓子, 带几分调皮, 唱了起来: 杜鹃花开郎思妹哟, 郎心妹心一样红哎……钟树有眨动着眼睛, 正入情地往下唱, 却忽然被脚下的吆喝声打断了: “好个老不死的, 快入土了, 这郎呀妹呀的哩!”随着声音, 从山道转弯处走出两个人, 一个是刘志顺, 一个是钟长兴, 他俩到乡政府开会, 路过这里。钟树有瞪着刘志顺说: “我快入土了?我还是民兵呃!”他转向钟长兴眨眨眼, “长兴, 我说的是真的吧?”“你不单想当民兵, 还想当新郎官呢!”钟长兴打趣道。“哎嗬——怪!啥年月啦, 还不兴我老有当新郎官哟!”钟树有指指我, “‘工作同志’说啦……怎说呢……对啦, 快进入社会主义啦, 分了田, 咱农友们的好日子才算刚开了个头……”“好, 等你搬进分到的新屋, 我第一件事就是给你保个大媒。哈哈哈, 新娘长得就象这杜鹃花一样, 免得你夜夜做梦都抱着杜鹃花……”刘志顺说说笑笑, 同钟长兴翻过山去。我第一次看到杜鹃花, 就爱上了它。折了几枝, 带回去插在搪瓷杯里, 果然给贫寒的小屋平添了几分光彩。自此以后, 钟树有经常从山上带几枝杜鹃花回来插, 不知是因为我欢喜这种花, 还是因为这种花寄寓了他的一种美好的希望。钟树有们对未来的生活寄予什么样的希望, 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自觉到自己翻了身, 成了土地的主人, 从今往后可以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 因为我们这些得到他们信赖的“工作同志”, 在“前途教育”中, 给他们描绘了一条金光熠熠的大道。不久, 钟树有搬进了分配的瓦屋。他从山上移来两丛杜鹃花, 种在他的新家的门前。工作队离村的时候, 正是杜鹃花开得最盛的时候。满山红杜鹃, 倒映在清冽的山溪中, 把山溪变成一条抖动的花团锦簇的彩绸。我望着山下挥别的乡亲, 心想他们的生活, 定如这被杜鹃花染红的山溪奔腾向前, 汇入壮阔的大江。几年后, 当我想起五岭山区的杜鹃花时, 心情却惴惴不安起来。多少次我想写信探问钟树有们, 却终于未敢提笔。我隐隐预感到那回信将使我面对怎样严酷的事实, 将搅乱那条在我心中流淌的给我以温馨回忆的山溪, 将击破我的同时也是我灌输给钟树有们的那个带着杜鹃花色彩的梦。……但我还是常想起那里的杜鹃花。在海南岛拖着浮肿的身子去找“革命菜”〔〕充饥的时候, 我想起过它; 在动乱的十年, 对着“牛栏”的窗口数星星的时候, 我想起过它; 我担心它的命运, 我默默为它祝福。五岭山区的红杜鹃常常象火一样, 在烧灼我的心。这就是我的绵绵的乡思呵!我不是望帝, 我不会化作杜鹃鸟, 但我的心在流血, 旦旦暮暮, 在漫长的岁月里默默地流血。直到今年初, 我从报上读到这个村子治穷致富的消息, 我才给钟树有们写了封信。一个月后, 一个提了盆杜鹃花的姑娘来找我, 她说她是钟长兴的女儿, 刚考上这里的一所大学, 是来报到的, 这棵杜鹃花是她父亲从山上挖的, 要她带给我。她还带来了一封她父亲写给我的信。钟长兴在信中告诉我, 钟树有一直没有成为新郎官, 大办食堂的时候死了——死于饥饿引起的浮肿病。刘志顺后来当了公社副主任, “文化大革命”中也死了, 是被打死的。他钟长兴算是幸运, 熬过来了。中央的三个一号文件, 使他过上了山里人心想的好日子。现在他成了编织专业户, 去年盖了五间新瓦房。信的末尾, 他感触很深地说: “要是土改后就这样办, 可有多好!”望着这棵来自山野的杜鹃花, 我低下了头。我能够想象到翻身之后死于饥饿和非命的钟树有和刘志顺临死时的痛苦心情。我感到内疚, 我想到我作为“工作同志”给山民们许下的诺言, 给他们编织的那个梦……一种责任感, 沉重地压迫着我。许多年来, 我自己虽然也处在十分恶劣的无能为力的境遇中, 但作为一个共产党人, 我不能推卸历史加在我良心上的重负。呵, 杜鹃花, 你这山野的火杜鹃啊!〔〕 革命菜: 生长在海南岛的一种野菜, 即野塘蒿, 当年琼崖纵队的战士常以此充饥, 故名之曰“革命菜”。
范若丁 人民日报 19850125


-
相关记录
更多
- 嘉兴杜鹃进北京 迎春绽放年味浓 2025-01-16
- 神州春色美 | 春日黑龙江 杜鹃开满山 2024-04-26
- 2023浙江森林旅游节暨第25届天台山云锦杜鹃节在天台开幕 2023-06-08
- 深入发掘鹿角杜鹃独特的园林应用价值 2023-05-25
- 安徽黟县五溪山杜鹃花盛开 2023-05-16
- 吉林龙湾举办野生杜鹃花卉旅游节 2023-05-08
 打印
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