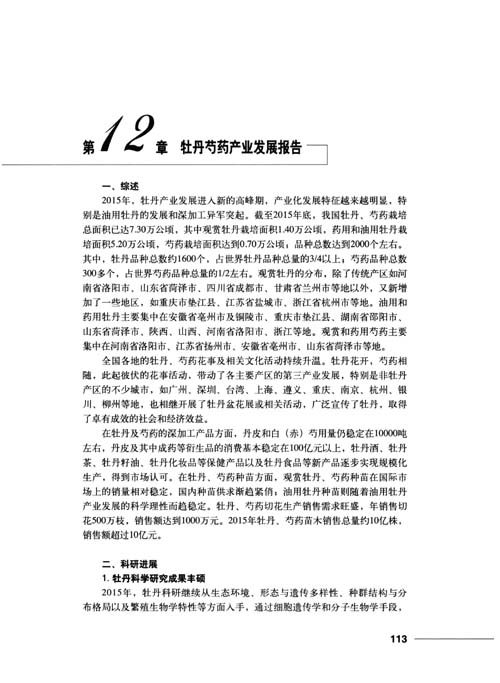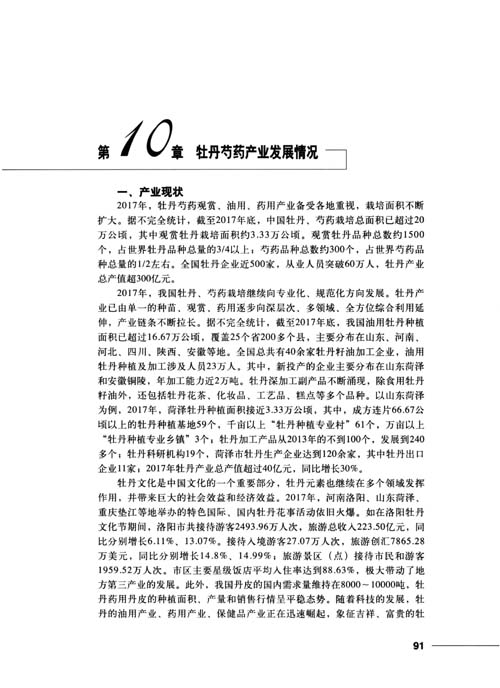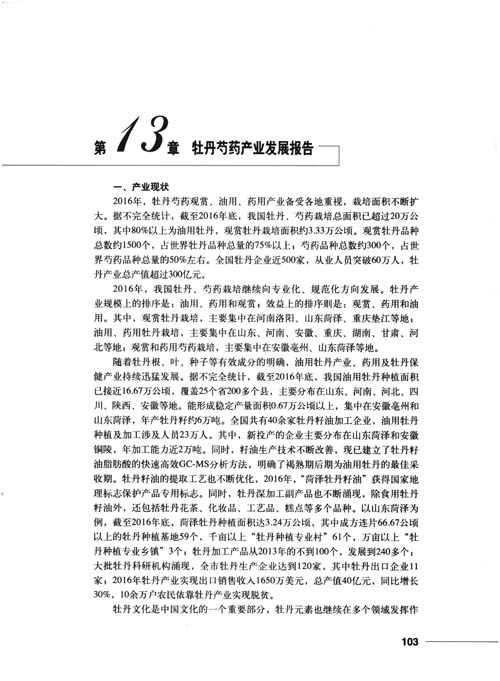延安牡丹
延安牡丹
刘成章
花瓣上的露水珠儿, 含着香, 常常滑落于梦中。
那花是延安牡丹。它开放在延安城西南二十公里的山谷中。地据花以起名, 那儿因之被称为花原头、牡丹山或万花山。现在一般叫万花山。
八十年代初, 万花山建起一座古色古香的豪华宾馆, 而与宾馆只一墙之隔的, 仍是原生态的陕北农村: 黄漠漠的黄土山洼, 碾子, 柴火垛, 鸡, 牛, 狗, 婆姨揭起门帘, 汉子闪闪地挑水归来, 杨木担子柳木桶。
东山的糜子西山的谷。上坡坡葫芦下坡坡瓜。
豪华与朴拙的强反差中, 耀眼的, 撩拨心弦的, 令人流连忘返的, 是千朵万朵的牡丹。
我国牡丹美艳者多多, 如洛阳牡丹, 菏泽牡丹, 巴蜀牡丹, 余杭牡丹, 等等。但是, 我敢说, 哪一个也没有延安牡丹来得那么奇绝。概而言之, 有八奇。
———奇一, 生在延安。
生在延安怎么叫奇呢?山在水在石头在, 山水石中, 自有原因在了。
唐代诗人皮日休赞牡丹诗云: “落尽残红始吐芽, 花名唤作百花王。竞夸天下无双艳, 独占人间第一香。”他把最尖端的词汇, 几乎全都献给了牡丹。
我国历代咏牡丹的诗词少说也有几千首, 在那些诗词中, 牡丹还被称为国色, 天香, 花君, 花帝, 等等。总之, 牡丹雍容华贵, 艳冠群芳。
所以, 牡丹历来总是植于富贵处所, 如宫苑, 京城, 并随着宫苑和京城的迁移而流转。
而延安是一个什么地方呢?跌死山羊摔死蛇。黄风刮来遮满天。古时候被称为化外之地。本世纪三十年代, 著名美国进步记者斯诺来到这里, 惊出一行文字, 有案可查: “人类能在这里生存, 简直是一个奇迹!”
但这牡丹, 却居然在这里生根, 发芽, 招展花枝, 开得满山满谷。这难道不是奇事一桩么?
———奇二, 野生。
别处的牡丹多是人工培植, 而延安的牡丹全属野生。荒山野地就是它的家。
荒山野地是没有园丁的。没人锄, 没人浇, 也没有多少人前来观赏。与它为伍的, 是荒草, 是野花, 是狐, 是兔, 以及一阵一阵的西北风。
荒山野地, 鸡爪爪黄连苦豆豆根。
所以宋代文学家欧阳修在《花谱》中说: “延安牡丹与荆棘无异者也。”他概括得极为准确。
但千百年来, 延安的牡丹硬是那么长着。它骨劲, 心刚, 有血性。
苦焦的延安!温差奇大。十年九旱。无肥。发一回山水冲一层泥。但它的牡丹酷寒挺身站, 大旱不低头, 就在极度贫瘠的土地上, 年年开花年年艳, 花香四溢。
———奇三, 不交易。
我国人民特别爱花, 所以牡丹自古有上市的传统。史载: 南宋时余杭的牡丹, “歌叫于市, 买者纷然”。唐代诗人白居易并有这样的诗句: “共道牡丹时, 相随买花去。”今朝更然。
可是, 开天辟地到如今, 花开花落千万年, 可以说, 延安的牡丹, 连一枝一叶都没有卖过。
鸡蛋常卖, 猪羊常卖, 粮食常卖, 就是没有卖过牡丹。
过去是没人买, 现在是舍不得卖。
这正好塑就了延安牡丹亘古以来的尊严。
延安的牡丹, 就像延安人的灵魂。
———奇四, 与柏树伴生。
万花山上, 尽皆柏树。山顶还有一棵奇柏, 叫五龙柏, 若五条龙凌空翻跃, 气壮山河。牡丹就长在这些柏树的根底。
柏树铁肌石躯, 牡丹玉肤腻体; 柏树森严, 牡丹活泼; 柏树阳刚, 牡丹阴柔; 柏树是英雄, 牡丹是美人。
顶着风, 遮着雨, 柏树呵护着牡丹。
牡丹花开, 是献给柏树的爱。
在我国的传统绘画里, 为了寄寓长命富贵的意思, 常把柏树和牡丹画在一起。但它们却在这儿天然地生在一起了。所以乡亲们极爱这片地方。尽管生活艰难, 他们从未离开过一步。
———奇五, 花好。
花朵大, 有的直径竟可达到六英寸, 像一个小碗。也美, 花开时节, 你看吧, 这一枝黄, 黄得像金; 那一枝白, 白得像银; 又一枝红, 红得像玛瑙, 像火焰, 像朝霞和晚霞, 像灯笼。复瓣的; 单瓣的; 半透明的。枝枝缤纷灿烂。枝枝艳若蒸霞。人都觉得那花枝中, 恍若闪动着仙子的脸, 仙子的姿, 仙子的裙。好像只要细听, 就能够听到花们的娓娓细语, 时而还夹带着欢愉的笑声。
它的色、香、味、韵, 无不透露着信天游一样的美质。
因此之故, 延安牡丹很早就声名远播, 隋炀帝曾命人将其中一些黄的移至宫苑, 被称为“延安黄”。
隋炀帝是一个以淫糜奢侈著称于世的帝王。他看中了延安的牡丹, 足见延安牡丹的不同凡响。
———奇六, 当柴烧。
《四库全书·关中胜迹图志》中有两处提到延安万花山的牡丹, 一处云: “其地多牡丹, 樵者采以供薪。”另一处云: “牡丹遍山谷, 樵者采之为薪。”并云, 欧阳修说的“延安牡丹与荆棘无异者也”, 就是这个意思。
当然更会以柏枝为薪了。
以牡丹烧火做饭, 谁曾见过?整棵的牡丹, 枝头花儿朵朵, 噌!噌!直往炉膛里塞!炉膛里噼噼啪啪, 分不清哪是火焰, 哪是花朵。做饭女子唱: “一对对喜鹊树上落, 快刀子割不开你和我。”这歌, 不知唱的是她的爱情, 还是炉中的情景。
是暴殄天物吗?是煮鹤焚琴吗?不能说。只能说是因时因地制宜。
外国也有类似的例子。好像是巴西人吧, 他们曾把海鱼作为肥料, 每撒一颗玉米种子, 就埋进一条鱼去。
那当然都是古往的事了, 现在自然不会。现在, 延安的牡丹贵重得就像金子一样, 整天有人看护着, 谁敢动它一指头!
不过想起古时的延安, 还是觉得特别有意思。
它烟囱里升起的缕缕炊烟, 含着多少奇香?它锅里做出洋芋擦擦, 红豆角角熬南瓜, 或者, 荞面圪羊腥汤, 是不是有如琼浆玉露?
哎, 莫看延安穷山沟里穿得烂兮兮的庄户人家, 千百年来他们所过的日子, 不是比隋炀帝还要高出几倍么?气死那些作威作福的家伙!
要是死了, 再让他死上一遍!
———奇七, 花旁出好女。
也许正由于上边所说的情况, 整年烧火做饭的延安万花山左近的姑娘, 便特别出众了: 古有花木兰, 近有蓝花花, 她们都名扬四方。
相传替父从军的花木兰就当当出生在万花山, 万花山的山顶上至今还存留着她的跑马梁。她也曾在这儿当窗理云鬓。现在人们在山下为她塑了像。
蓝花花呢, 也出生在离这儿不远的村庄。她美艳照人, 敢于向命运抗争, 硬是盖倒了一十三省的女孩儿!
因为她们, 古诗《木兰辞》和现代民歌《兰花花》, 一个接着一个脱颖而出, 瑰丽了我国的艺术宝库。于是, 意念中的她们更美了, 花木兰的脚下踩着动听的诗韵, 蓝花花的腰肢扭出美丽的旋律。
历史的天空被云彩遮住了吗?诗与歌, 是风。唧唧复唧唧。青线线。蓝线线。暮宿黄河边。冒着性命往哥哥家里跑。一疙瘩云彩风吹散, 她们既有牡丹的美丽, 又有柏树的刚强。
———奇八, 可以说是最大的一奇, 它好像身怀障眼法。
战争年代在延安生活过好多年的老同志, 十有八九都没见过延安的牡丹。
延安有多大?有北京的千分之一大么?但是, 他们在延安生活了那么些年, 却硬是浑然不知!举个例子吧, 1986年, 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到延安考察, 他见了万花山的牡丹, 惊诧地说道: “我在延安生活了八九年, 怎么连听都没听过呢!”
这真是奇而又奇的事情!
人们历来对于牡丹, 都是青睐有加。唐代诗人刘禹锡在形容长安赏牡丹的盛况时有诗云: “唯有牡丹真国色, 花开时节动京城。”
可是怪了, 当年延安的花开时节, 这些老革命都到哪儿去了?
去哪儿?哪儿也没去!开荒中有他们的身影, 纺线中有他们的身影, 整风中有他们的身影, 保卫延安中有他们的身影。
但是他们为什么根本没看到延安的牡丹呢?恐怕只能有这样一个解释: 时代的注意力所致。
那时候, 时代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革命上了, 眈眈向一, 绝无他顾, 全神贯注, 埋头苦干, 以致忽略了对美的欣赏。
怎么会呢?为什么会呢?真实吗?
凡是熟悉陕北民歌的人, 不会不知道这样一首: “骑白马, 挎洋枪, 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的粮。有心回家看姑娘, 打日本来顾不上!”这民歌, 正好对此做了一个有力的证明。
那是一种神奇的精神辉煌。明明是眼皮子底下的美景, 却视而不见。而且不是十个人, 八个人; 是成千上万, 是整整的一代!
时代把人们的精神都聚集到伟大神圣的事业之上去了。一杆杆红旗半空里飘。镰刀斧头老镢头, 砍开大路穷人走!其他物事即使再美好, 也失去了诱人的力量, 也被冷落一旁。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啊!热血沸腾。无私奉献。前仆后继。背负着民族的希望。向前, 向前, 向前!
为了全国花开遍, 不知延安有牡丹。
那精神, 奇艳如延安牡丹!
《人民日报》 〔19980206№K〕
刘成章 人民日报 19980206


-
相关记录
更多
- 牡丹江“花经济”绽放新活力 2024-04-29
- “小蘑菇”长成“大产业”——牡丹江食用菌产业发展见闻 2024-04-25
- 黑龙江省林草局与牡丹江政府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2024-04-24
- 2024北京牡丹文化节启动 2024-04-24
- 河南洛阳牡丹盛放 2024-04-22
- 河北柏乡:第十一届汉牡丹文化节开幕 2024-04-21
 打印
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