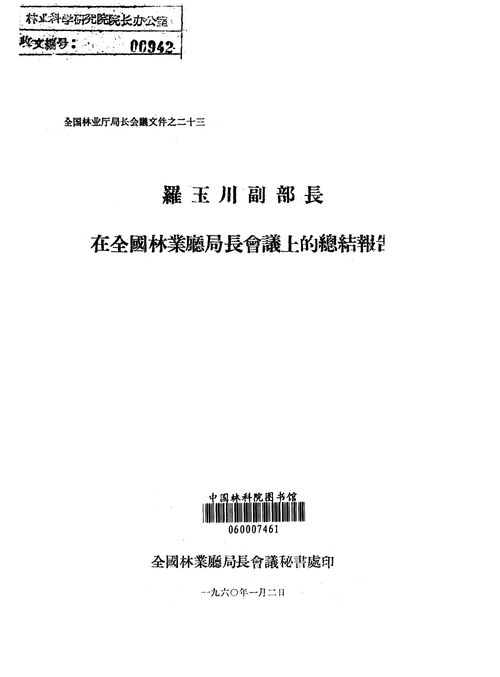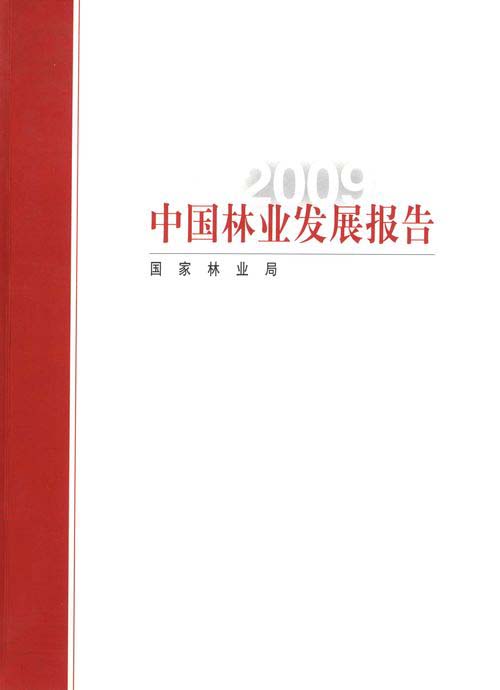徐凤翔: 一息尚存 不落征帆
题记:
一个一个、一群一群、一批一批知识的苦力, 智慧的信徒, 科学与文化的“朝佛者”啊, 我们也是一步一步跪地在险路上走着。恁是怎样的遭遇, 我们甘心情愿, 情愿甘心。
——摘自徐凤翔的“科学知己”、作家黄宗英报告文学《小木屋》
“感谢各位朋友冒着暑热, 来给我这个‘80后’老太婆捧场。”前不久在中国环境出版社举行的《高原梦未央》发布会上, 新书作者、生态学教授徐凤翔向与会者颔首致谢。
白色的短衫、褐色的长裙、表情丰富的眼神, 轻盈的脚步、敏捷的思维、壮心不已的豪情……让人忘了她的年龄——82岁。
“我有幸终生从事林业研究和生态环保事业, 受教于大自然。尤其是在年近半百之时, 往返跋涉于大高原的苍天厚土……”在随后举行的“走进高原深处”报告会上, 徐凤翔娓娓道来, 回顾她倾其一生的高原梦、生态情。
46岁单身赴藏, 开高原森林生态研究先河; 65岁下高原, 在北京灵山创建第二座“小木屋”, 传生态保护之道; 80岁再著新书, 报高原培植之恩、还亲友相助之债……
讲者动情, 听者动容。
1
科学“文成公主”带着嫁妆进藏
1931年, 徐凤翔生于江苏丹阳。江南水乡的灵秀、家庭教育的熏染, 让年少的她做起了文学梦。一个偶然的机会, 却把她引入“林家大院”。
那是1950年, 徐凤翔在照顾中风卧床的父亲之余, 常跑到附近的新华书店看书。一次, 她无意中读到《中国林业杂志》创刊号上新中国首任林垦部部长梁希的文章: “把河山装成锦绣, 把大地绘成丹青, 新中国的林人同时也是新中国的艺人……”诗意的语言, 特有的时代激情, 让她转入“林家大院”。
南京大学森林系毕业后, 徐凤翔被分配到南京林学院(南京林业大学的前身)任教。此后的20余年里, 除了日常的教学科研, 她特别钟情于野外考察。长白山林区的松涛, 阿里山的密林……徐凤翔考察了除西藏之外的主要林区, 为后来的高原生态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77年, 南京林学院接到援藏任务: 派一名森林生态学专业教师赴藏任教。获知这一消息, 已是人到中年、儿女成双的徐凤翔热血沸腾。她说服了家人和领导, 终于获准入藏。
任重道远赴边疆, 夕照征途鞍马忙。无须反顾江东岸, 留得余晖育栋梁。徐凤翔以诗言志, 与丈夫范自强道别。
经过艰苦的长途跋涉, 年近半百的徐凤翔由川入藏, 独上高原。到达位于林芝地区的西藏农牧学院后, 她热泪盈眶: 经过20余年的向往和争取, 终于进门了, 归家了!
除个人衣物, 徐凤翔还带来了测树、测土、林分调查、气象观测的教学用具和一批专业图书。农牧学院的段书记笑称: 科学的文成公主带着嫁妆进藏来了。
2
奠西藏森林生态研究之基
两年援藏期满, 徐凤翔赴京汇报, 她向国家科委力陈开展西藏高原生态研究的意义, 申请创建高原生态研究所。经过6年的多方吁请, 54岁的徐凤翔于1985年正式调藏, 重上高原。
建所报告通过后, 她连续三天“赖”在自治区副主席拉巴平措的家门口。拉巴平措深受感动, 特批60万元经费。徐凤翔精打细算, 在尼洋河畔建了一座2600平方米的科研小楼, 购进了一批观测设备。这座以木质结构为主体, 集办公、住宿、观测、育苗于一体的“科学小庙”, 被她亲切地称为“高原小木屋”。
“科学小庙”规模虽小、人员虽少, 却是我国高原生态研究的摇篮。徐凤翔的爱人范自强利用假期赴藏, 帮助设计建设了分析实验室。除了在所内建立常年定位站, 研究所还在农牧学院和色季拉山的东西坡上设立了观测点, 常年开展森林生态定位研究, 观测、采集了林分生长、树冠径流、地表植物等科学数据。
野外考察是研究所的重头戏。从海拔800米的亚热带林区到5400米的珠峰大本营, 从不通公路的墨脱到人烟稀少的那曲, 从道路奇险的金沙江两岸到崖陡流急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徐凤翔野外考察行程12万公里, 其中骑马2000多公里、步行近3万公里。通过实地考察, 她获得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数据、标本和图像资料。她带领同事对西藏的主要生态类型, 特别是森林类型的生物组合、结构和生长、分布规律、资源价值、保护利用方法等, 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分析, 创立了西藏森林生态学, 并推动了林芝云杉林、巨柏林、墨脱林区生态与珍稀物种等西藏多个自然保护区的建立。
塌方滑坡、蘑菇中毒、疟疾发作、蚂蟥叮咬、狼群围困……面对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 徐凤翔处之泰然、从容应对。
如今, 藏东南地区的一些老人依然能记着她当年的光辉形象: 上下鼓鼓囊囊(仪器设备), 左右瓶瓶罐罐(土样、水样标本), 遇车伸出“熊掌牌”(途中招手, 请求搭便车)。
常有人问: 你不寂寞吗?徐凤翔如实相告: 寂寞, 也不寂寞。野外科考时, 有丰富多样的树木草虫为伴, 哪来寂寞?回到研究所忙于资料整理, 没有时间寂寞。
人非草木, 孰能无情。闲暇之余, 孤独寂寞和思亲之情悄然来袭。“妈妈把草木当人养, 把我们当草木养”——想起女儿的抱怨, 她更感内疚。晨昏月夜, 遥望千里之外的江南小家, 徐凤翔只能自我排解!
3
创建北京灵山小木屋
“华夏西隅, 登高纵览: 观高原无限, 雪峰高耸……而今自然灾害频发, 人为索取不断, 绿荫褪色, 大气增污……更令人堪忧者: 社会阶层多陶醉于建设之快速, 沉湎于消费之繁荣, 游乐于伤残之山水, 而较少为生态危机忧患, 为保护生态竭力。想吾世人, 应直面神州, 自思自检, 及时醒悟, 善待自然……”
这段发人深省的话, 来自徐凤翔构建的第二座小木屋——北京灵山小木屋。
1995年, 由于身体原因, 在西藏工作18年的徐凤翔离开了她眷恋的大高原。她本可以在家含饴弄孙、颐养天年, 但未竟的高原之梦, 时时萦绕于心头: 一是为雪域高原正名——西藏并非荒凉的“生命禁区”, 而是生态类型多样、物种丰富的风水宝地; 二是开展环保科普教育, 传播生态保育之道。
走下高原的她再上灵山。位于北京西郊的灵山, 海拔2300多米, 徐凤翔称之为“北京的珠穆朗玛”。经多方游说、化缘, 北京灵山生态研究所终于在1995年12月正式挂牌。最大的“贺礼”, 是从藏东南运来的一批花草苗木, 包括高原生态研究所的“所树”林芝巨柏和“所花”西藏黄牡丹。
造型装饰很像西藏小木屋的灵山生态研究所, 内设中国高原纵览展室、灵山生物多样性展室、生态教学楼等。院内的80余亩园圃和温棚, 引种成活了来自西藏和其他地方的近百种乔灌草植物。10多年来, 灵山生态研究所先后接待参观者两万多人次, 被誉为“独特的生态科教园地”、“绿色的藏汉团结纽带”。徐凤翔本人和她的研究所, 分别获得我国的环保大奖——“地球奖”。
4
情系大自然 高原梦未央
此生阅历千重山, 心波浩渺难驻鞍。古稀之年的徐风翔依然壮心不已。2001年, 70岁的她再上高原, 考察珠穆朗玛冰雪荒原、藏北高寒草原—草甸、藏东南色季拉山林区; 2002年, 考察新疆北部的阿尔泰—喀纳斯、天山—伊犁和塔里木河胡杨林区; 2003年, 考察滇西高黎贡山、梅里雪山、泸沽湖林区……
之后, 她又东赴日本、北飞美洲、南下亚马孙……通过生态对比性考察, 徐凤翔对生态保护和资源利用有了新的感悟。
一路走来, 一种负债感油然而生, 挥之难去: 自己大半生奔走在大自然、大高原的天地间, 深受自然万物启悟之恩、身负社会亲朋相助之债。所受大恩, 焉能不报?身负大债, 岂能忘还?
一介书生, 只有以文相报。80岁时, 她决定再写一本新书, 以报恩偿债于万一。
此前, 徐凤翔已出版《森林生态系统与人类》、《中国西藏山川植被》、《西藏高原森林生态研究》、《走进高原深处》等多部著作。在她看来, 这些以专业论述为主的书, 未能反映自己数十年专业考察中的“景中之情”。
在新书写作中, 先是老伴范自强猝然离世, 后是自己被查出肠道肿瘤……以“一息尚存、不落征帆”为座右铭的徐凤翔没有倒下, 坚韧前行。经十年酝酿、三年熬炼, 图文并茂、情理交融的《高原梦未央》终于付梓。
在新书发布会上, 她把自费购买的2000本书分赠给大家: “希望今天在场的朋友都能当我的邮递员、通讯员, 把自然之道传递给更多的朋友。”
“80后”老太说, 她将继续赴国外进行生态考察, 计划三年内再写两本书。(赵永新 方草山)
人民日报 2013-9-10


关键词 林业建设
-
相关记录
更多
- 贵州:不负青山的奋斗足迹 2025-02-06
- 上海金山绿化林业建设融入健康理念 2024-04-17
- 浙江省级总林长会议要求加快建设高质量森林浙江 2023-04-07
- 安徽宣城:积极探索科技防火 助力智慧林业建设 2023-03-21
- 国家林草局印发《全国林业工作站“十四五”建设实施方案》 2022-06-23
- 《全国林业工作站“十四五”建设实施方案》印发 2022-06-23
 打印
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