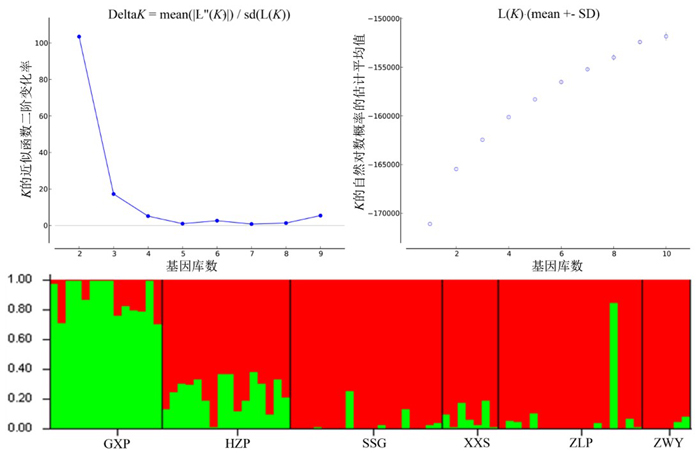乌蒙杜鹃
画花鸟的朋友从乌蒙山区访杜鹃回来, 告诉我: “这回是眼见为实了。以前听你形容得那么玄乎, 我还真有点不敢相信。”
是的, 乌蒙杜鹃的气势, 若非亲眼得见, 是难以想象的。
记得我去到那所大山皱折里的民族中学的第一个晚春, 女生们星期日下午返校, 三三两两捎来几大捧野花, 我的小屋都盛不下了。我诧异怎么人同此心, 她们说, 这花开得满山都是, 招人去折, 又都想城里人爱看花, 便不约而同了。
那花真有点慑人!一朵朵足有菜碗那么大, 颜色有大红、雪白和粉红。叶子象枇杷叶而略细长, 厚厚的, 正面墨绿油亮, 背面有一层鹅黄的茸毛。仔细看看, 原来每朵大花是由好几朵小花簇聚而成。那花形很眼熟。问女娃们, 说是叫“映山红”。我这才恍然: 单看一小朵, 可不就是常见的杜鹃花么?
恰好, 从嘉陵江边来了个看山的青年人, 我们就一道去寻访这种奇异的杜鹃。走的是一条当年红军长征的故道。学生们介绍, 这条路上映山红特别多。
可不是!我们离开小镇不远, 步入莽莽群山的边沿地带, 成片的杜鹃花就泼头盖脑地迎过来, 把我们掩没在重围之中。纯乎不是我们见过的、想象得出的杜鹃, 它是高树!是森林!我们猝不及防, 连呼吸都屏住了。后来曾想把这个印象记下来, 却无法把绚烂的感觉变成传神的诗句。只是说, 杜鹃象迸发的山泉, 溢出壑谷, 涌上山巅; 说它伴随着蒸腾泥香的梯土、笼罩绿烟的秧田, 烘染得山里的春光火红、灼热、醇酽。还想象是第一阵春雷在云端隆隆震撼, 火星儿满天迸溅, 化成了这万千春花……
当时青年朋友向一棵高达丈余、红色大花足有上千朵的杜鹃花树奔去, 惊飞了一对拖着长尾巴的彩色小鸟(这种鸟在当地名叫“梁山伯祝英台”)。他爬到枝杈上让我拍照, 嘱咐我一定得照好。因为他的同学们决然不会相信, 世上有这样巨人般的杜鹃花, 必得有照片为证。
我理解他的心情, 我自己也需要这样一张照片为证。在山区和丘陵地带, 杜鹃花绝非稀罕物事。童年时在家乡听姐姐们唱过一支歌, 说是在淡淡的三月天, 山坡上小溪旁开着杜鹃花, 象美丽的村家小姑娘。成年后一次出差, 乘货车行驶在大山丛中, 沿路一蓬蓬鲜红的山杜鹃, 象绿海上浮动着星星点点的火苗, 给人一种幽丽而落寞的感觉。车停在一眼山泉边加水。我站在阒无人迹的公路上闲眺, 不提防真看见了一个村家小姑娘, 是个彝族女孩, 站在一丛映山红旁边, 摘下一朵朵花儿, 把花蒂放在唇间吮吸(我从小就知道, 那花汁酸甜酸甜的)。一边还惬意地把赤着的脚丫子一只擦擦一只。几头白羊黑羊挨挤着她, 盯着那四只轮子的庞然大物, 惊惶地咩咩叫唤。小姑娘愣一愣明媚的细长眼睛, 用轻声叱骂来安抚胆小的羊儿……就连这幅图画, 也透着三分寂寞。
而现在, 绿海中一星一点的火苗, 变成了熊熊的野烧。不, 简直是天然气的爆炸!这是一篇李太白的古风, 纯以磅礴恣肆的气势取胜。满眼的火红, 转化成浑身的灼热。这真是一次撼心慑魄的体验!
杜鹃花在这一带特别繁茂, 据说是因为地下有极丰富的煤矿。农民常根据杜鹃的疏密来开挖小煤窑。至于杜鹃花如何与煤矿结下不解之缘, 那得请教土壤学家或生态学家了。我只是痴想: 莫不是地下的煤层把炽热的本质注给杜鹃, 它才具备了这样火辣辣的性格。
在富于想象的人民当中, 它是否也同“望夫云”、“神女峰”和各地的奇山异物一样, 也拥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呢?确实如此。我听到的一个传说, 与长征边境的红军联在一起。
故事的前半段很一般化: 红军巧设“张灯诱蛾”之计, 歼灭了连夜追袭的民团。故事的结尾, 却颇有浪漫主义色彩。暗夜深沉, 战斗中坠岩断腿的农民向导, 强逼着为救他也负了伤的红军战士, 撇下自己去追赶队伍。他们依依不舍地分了手。在黎明前的漆黑中, 向导看见红军伤口里流出来的血, 象松明的膏火一样, 燃烧着卜卜地滴到地上, 把草茎也照得清楚可辨。他凭借着这些鲜血燃起的火星, 目送着红军步步远去。第二天, 这一路的杜鹃树, 提前一两个月开了花, 比哪年都繁盛, 红得象血, 亮得象红军的眼睛……
红军战士的血, 象松脂般燃烧着溅进泥土。这真是个动人的想象。当年, 这一带不知有多少青壮年农民, 被红军的赤诚点燃, 跨进这支队伍。为我中华民族永作自由人, 他们绝大多数在异乡的山麓水畔埋葬了忠骨, 再也没有音讯回到家乡。
但也有个别的幸存者。就在我们饱看了满山杜鹃的两年后, 一位当年随红军北上的民fū, 后来的解放军少将, 解职回乡来了。他的家乡有一个突出的标志: 一座高耸入云的酷似雄鸡的巨岩。百里方圆内都能看到。地方也因它而得名。消息震动了附近的村镇。但我始终没有机缘见到这位将军; 也不知道最后他是重返首都了呢, 还是已经长眠在故乡的土地上, 象几年后读到的小说《小镇上的将军》里的主人公。
每当暮云收尽, 我常兀立在小楼窗口, 久久眺望三十里外那只引吭入云的石鸡剪影。解甲归田的老将军, 他正在做什么?他如今用什么方式, 打发这慢悠悠慢悠悠的乡居日月?每次, 我总是无来由地回到辛稼轩的那两句词“醉里挑灯看剑, 梦回吹角连营”。我确信他不会享受到恬静的林下生涯, 因为深重的灾难重新笼罩着神州赤县, 再近视的眼睛也看到了满目疮痍。平头百姓尚且在为国家的命运忧心如焚, 何况为人民政权厮杀半生的老兵!我从石鸡联想到祖逖, 我想象老将会象那位晋代的名将, 在第一声鸡鸣中跳起来, 唤醒身边的儿孙: “此非恶声也!”然后执三尺青霜, 在硕大无朋的金鸡脚下奋然起舞。我常想, 他是不是盘桓在杜鹃林中, 用指尖触摸着血一样的花瓣, 回忆起吴戈犀甲的岁月?他知不知道那个关于杜鹃花的传说?当他听到这段故事, 是不是为那位战友的碧血和民的断脚, 沁起过火辣的泪花……
在那场旷日持久的浩劫中, 人人自危, 岌岌不可终日。独有绚丽而无任何观点的杜鹃花树是超脱的吧?可有谁知道, 连它也在劫难逃呢!农民们忽然大肆砍伐起杜鹃林来。后来听说, 这是学大寨运动的统一部署; 是一箭双雕的妙策: 既把荒山变成了粮仓, 又可以用杜鹃树干做成木碗, 作为特种工艺品换取外汇。说是有关部门已同某国签订了十万只漆器木碗的合同。于是, 素以勤劳听话著称的社员们, 组织起大兵团, 开荒、砍树、做木碗。那些本来就因地广人稀, 耕作极端粗放的大片耕地, 更加置之干部的度外了。这场壮举的成果, 毫厘不爽地符合种瓜得瓜的规律: 既没有新粮仓, 也没有木碗。没有了杜鹃树林, 也没有了水土保持。
当我告别这座大山皱折中的小镇时, 敞篷货车再一次经过那条长征故道。那片曾叫我们如醉如痴的花海, 只剩下七长八短的一片黑色残桩。活象在凭吊一块尸骸狼藉的古战场。我想起, 为了招来那位远方的青年人再度进山, 曾诌过几句诗寄给他, 末尾说: “江边佳客再来否, 又是杜鹃如海潮。”一旦他真的再来, 就给他看这个吗?我禁不住生出一缕幻灭的苍凉……
如今, 那位花鸟画家的《乌蒙杜鹃》已经展出, 引起了众多的反响。而我离开那山花烂漫之乡, 转眼已六七年了。画家既是亲眼看到了火海一样的杜鹃花, 可见杜鹃林依然无恙。这是那场砍伐运动中的幸存者呢, 还是那些倔强的断桩又长出了新林?管它哩, 杂花生树、群莺乱飞, 怎么说也强似高天寒流滚滚、大地白茫茫一片干净吧!但我仍然私心祈望, 它是那场劫火里复生的凤凰, 就象我们的祖国和民族。
我想再给年青朋友写一封信, 邀他联袂重访那片碧血化成的杜鹃林; 顺便打访一下那位老军人的下落。
⒈ 赵志方
戴明贤 人民日报 19810228


-
相关记录
更多
- 嘉兴杜鹃进北京 迎春绽放年味浓 2025-01-16
- 神州春色美 | 春日黑龙江 杜鹃开满山 2024-04-26
- 2023浙江森林旅游节暨第25届天台山云锦杜鹃节在天台开幕 2023-06-08
- 深入发掘鹿角杜鹃独特的园林应用价值 2023-05-25
- 安徽黟县五溪山杜鹃花盛开 2023-05-16
- 吉林龙湾举办野生杜鹃花卉旅游节 2023-05-08
 打印
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