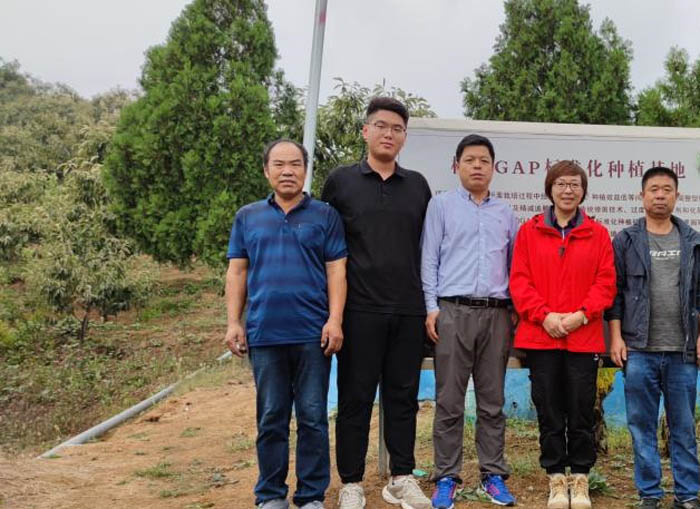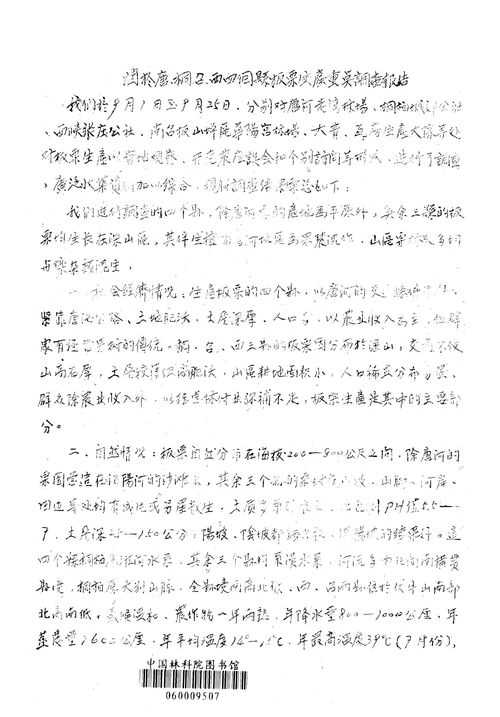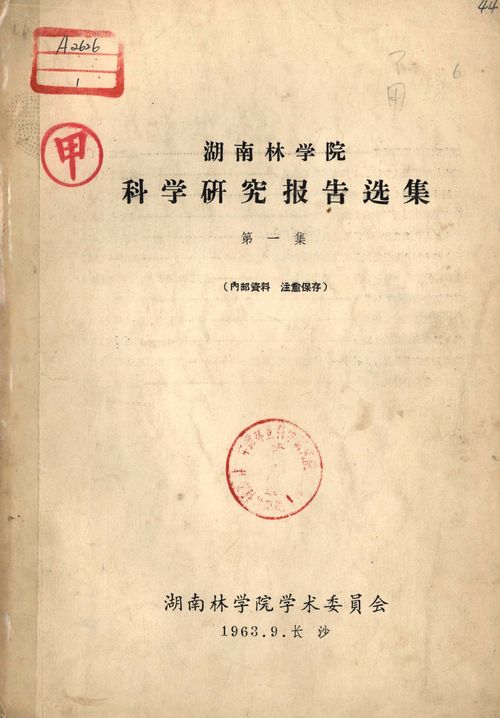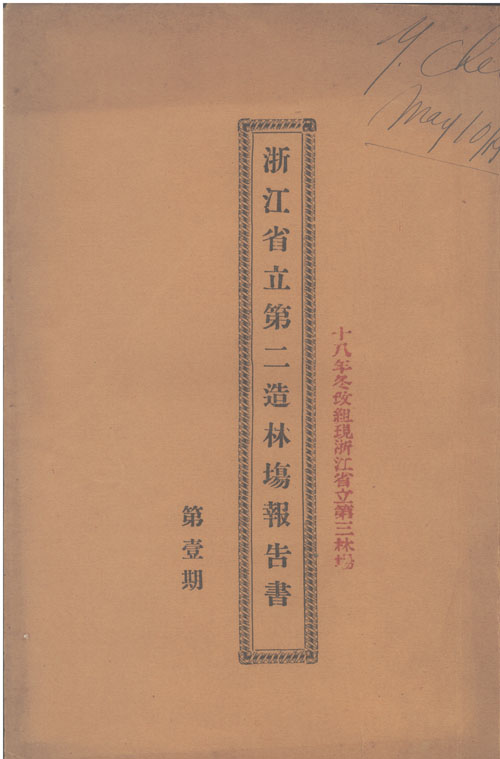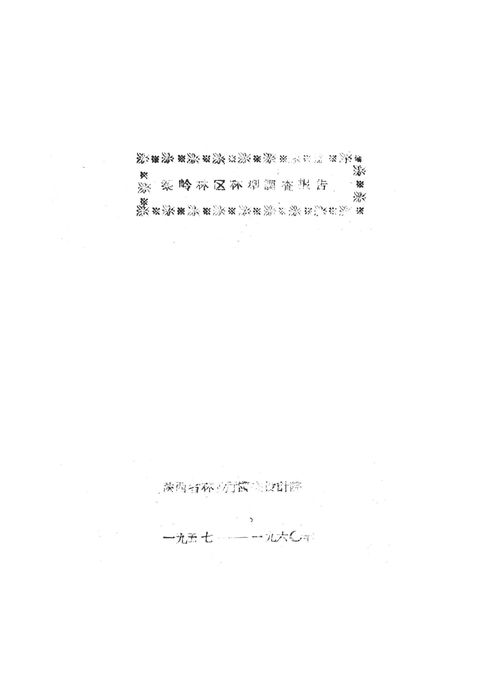家乡的板栗
我的老家在长江西陵峡北岸。它虽然比不了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但也山清水秀,物产丰富,是有名的板栗之乡。
在这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栽有板栗树。这些板栗树就像他们的的孩子,维持着他们的生存和希望。对每一棵板栗树,他们都有一本账,心里总是一清二楚。
板栗树的命很贱,对环境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它不用施肥,几场春雨过后,老树、新枝便换上了绿装,在一片春色中挤着笑脸。疯长的枝条在阳光下无拘无束,泛绿的树叶在微风中自娱自乐,寂静的山村便因此多了几分生机、有了几分灵气。
6月一过,板栗花谢了,落在地上,像一条条毛毛虫。它除用来引火之外,还可以熏蚊子。板栗的果实跟仙人球差不多,只是个儿小一些。乡下人给它取了个很土的名字,叫 “板栗苞子”。苞子刚泛青时,我们的心就痒痒起来,实在馋了,就偷偷往树上掷石子,以便把它们打落下来。苞子一落地,我们就用石头的钝角轻轻砸开绿油油的壳,迫不急待地分享一瓣瓣尚未成熟的秋天。其实,嫩嫩的板栗仁还只有汁液,嚼在嘴里还带着苦味儿,但我们仍然吃得津津有味,好像它就是天底下最好的风味美食。
待到板栗苞子成熟的时候,刺猬一样的果子便相继裂开了嘴儿。风一吹,有些熟透的板栗果从苞子里掉了下来,钻进厚厚的落叶里。那时,念小学的我们常结伴到别人的山上去 “打游击”(拣板栗)。淳朴的乡亲们见了,一般都不会做声。可有时候,我们嫌拣得少了,就动起手来,朝树上的板栗进攻。够得着的板栗用树枝打,够不着的用弹弓射或石子掷,有时就干脆上树去,猛地摇晃几下,让金黄的板栗苞子像雨点一样落下来。我们则像一只只小刺猬,四处乱窜,疯狂寻找。有的掉下来时,板栗与苞子壳就分了家。没有分开的,我们用鞋底踩住,然后使劲一搓,黄晶晶的板栗便从壳中露了出来。要是碰到一颗特别大的板栗,我们便互不相让,甚至免不了一番争斗……
这样,我们的吵闹声就惊动了板栗的主人。他们总是慢条斯理地喝斥着:“这是谁家的孩子呀……”眼看声音越来越近了,我们才揣着鼓鼓的衣兜落荒而逃。可很多时候,我们因为得意忘形,最终还是被逮住了……结果可想而知,板栗归我们,父母的巴掌也归我们……巴掌像雨点一样落在屁股上,比当时摇落的板栗掉得还快,来得还猛然,那火辣辣的疼痛,比被板栗苞子扎了还剌激,只是那滋味儿,远远没有板栗那么香甜,那么持久……
如今,我来到了城里。每逢金秋十月,乡亲进城,准会给我捎来家乡的板栗。当香甜的板栗汁儿沁入心脾时,我又仿佛回到了童年时光,也想起了那些淳朴的乡民,仿佛看到他们面对硕果满枝的板栗,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谭志 中国绿色时报 2004-7-15


-
相关记录
更多
- 推动板栗向轻简生态友好型栽培跨越 2024-03-27
- 陕西佛坪板栗销往港澳 2024-03-21
- 云南永仁千余名板栗种植户参加冬季修剪技术培训 2024-02-20
- 迁西有个巧种板栗的史正宽 2023-09-28
- 陕西商洛:“数字板栗”开辟生态产业发展新路径 2023-06-01
- 山东泰安举办板栗优质丰产栽培技术培训班 2023-03-28
 打印
打印